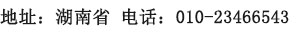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平安医院 http://www.bdfyy999.com/m/
年冬,诗人穆旦在西南联大写下“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西迁是被历史洪流裹挟而身不由己的寂长“流放”,或者更像是一场向死而生的精神远征。
年,原计划继西南联大之后迁校昆明的华中大学应爱国商人严子珍之邀,转赴大理喜洲办学。三月青衣,苍洱的风拂去异乡人通身的风霜,在时空偶然和必然的夹缝中备下天地应和的长筵。
出于习惯,总会在文字叙述中回避浓郁而用力的形容词,直到我在喜洲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看到一墙老照片,黑白且模糊,却因一人一事一地定格的表情让照片之外的人真切感受到八十年前细密柔暖的日光,那一群在抗战烽烟中弦歌不辍的青年,他们热烈、痛快、鲜明。
那些年轻人喜欢在洱海边走动,有高原上不羁的太阳,眼前净静的湖泊是苍山投映的虚像,正如他们站在历史沉重的背影后找寻到另一种生的暖意,在满饮饱食生命的艰酸之后炽热而真诚地活着。起初,只是这些来自大城市的教授学生在一个僻远的小镇延续着“格格不入”的习惯,尽管破旧却保持整洁的衣着,虽然难以相通但谦和有礼的语言,即使物什简陋也依然坚持的新式生活习惯,是随风入夜的雨,因一所学校的到来,文明开化的新风在喜洲古老的空气中弥漫渗透。可能喜洲让世人可见可感的第一个文明符号是电灯,而真正旷久代续的“文明”是老舍先生在造访喜洲时发出的惊叹,地方士绅竟捐资一百多万为中学建起了阔气的楼房!
在时境覆压之下与光阴的激烈博弈,西迁师生的行止言动都有了“痛快”之感,这种“痛快”是希冀科学救国的内心紧迫,也是前途晦明不定下奋起的自我救赎。是心境决定的环境,身边长狭的湖也是学术无尽的水域,他们潜心研究洱海中繁杂的生物引起世界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