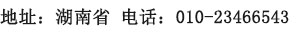上海夏天的香味离不开用细铁丝串起来的一对白兰花。每年快要到黄梅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阿婆提着竹篮开始卖白兰花。
小小的花,淡淡的香,花瓣上的雨露剔透晶莹,低调又粘人。一声甜糯的“栀子花,白兰花”,就会勾起很多人心底的千转百合,熟悉又遥远。今天,是上海发布享读第24期推送,我们一起来看看上海作家谈瀛洲教授写的外婆和白兰花的故事。
音频由“上海新闻广播”提供
诵读:雪瑾(《直通》首席主持人)
阿婆胸前的纽扣上
常常挂着两朵白兰花
我的阿婆是很喜欢香花的。我们小时候,她时常会给我们学她童年生活在苏州时,卖花的小贩兜售香花时的叫卖声:“栀子花,茉莉花”,“栀子花,白兰花”……
我父母在我四五岁时离开上海去支内之后,家里剩下两个分别比我大11岁和8岁的姐姐,还有一个比我大6岁的堂哥。我们的生活都要靠阿婆一个人照顾。现在想想,压在她身上的担子,真的是很重啊。
那是计划经济的匮乏时代,买许多东西都要凭票。去粮店买米要有粮票和购粮证,买油要有油票。
去菜场买菜那就更复杂了,买肉要有肉票,买鱼要有鱼票,买蛋要有蛋票,买豆制品要有豆制品票。过年时,还有专门发的买过年用的鸡票、鸭票等。各种票证一大把,连我看着也头晕,真不知阿婆是怎么搞清楚的。
尽管有了票,但买菜还是要早起去菜场排队,不然就会买不到想买的东西。阿婆一般四五点就起床去买菜了,回来还常说有比她去得更早的。有两三点去的,过年时甚至有半夜就去的。还有在这个队伍里摆块砖,那个队伍里摆个篮子,同时排几个队的。
那时,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常常和阿婆睡一张床。二楼亭子间里放了两张床,堂哥睡一张单人小床,我和阿婆睡一张双人大床。两个姐姐睡二楼的前厢房,那里原来是我爸妈的房间。
有时后半夜在睡梦中醒来,看到窗外还是黑洞洞的,六十多岁的阿婆却已悄然起床,在她身后轻轻带上亭子间门,出去买菜了。然后到六点左右她又匆忙从菜场奔回,给我们这些小孩准备早饭,叫我们起床上学。
那时我就在想,等我自己长大后,该怎么应付这种生活。所幸是长大后,市场经济来了,菜场白天也开门,除了晚上,什么时候都能买到菜。我童年时担心的问题消失了。这才意识到,当时的匮乏,不过是一时的匮乏。
夏天的时候,外婆从菜场赶回家,胸前的纽扣上就常常挂着两朵白兰花。这种花在我的头脑里,就和辛劳的阿婆和她对我们的照顾联系在了一起。
就着酱菜、腐乳吃泡饭
那时候的早饭,说来也简单,平常就是隔夜的米饭和饭粢(锅巴)烧的泡饭,就着酱菜或者是腐乳吃。
酱菜的话除了萝卜丝外,偶尔还能找到脆脆的宝塔菜,就像是有许多节的微型葫芦。因为少,所以我觉得很稀奇,吃粥时常常在酱菜里找宝塔菜。
我的早饭还比别人多一瓶牛奶。那时牛奶也不好订,有限额,家里只能订到一瓶,就给我这个最小的孩子吃。
每天大清早牛奶公司就会送来,装在一种瓶壁很厚的玻璃瓶里。阿婆平时把牛奶煮热了给我吃,稍凉后表面会结起一层奶衣,我用筷子把它先撩起来吃掉。
夏天时我会要求吃冷牛奶,就直接倒在滚烫的泡饭上,拌着泡饭吃,这样泡饭就不烫了。
那时学校每年总会组织一次春游和秋游。碰上这种时候阿婆就会买粢饭团给我吃,她说那个更“熬饥”。
等我大些了她就会给我钱,让我自己去东台路、浏河路街角的那家早餐店去买。这家店在清晨总是热气氤氲,里面卖甜大饼、咸大饼,还有油条、粢饭糕和粢饭团。
卖粢饭团的老师傅揭开一个大木桶的盖子,里面是用白布裹好的一大团热气腾腾的糯米饭。老师傅会用戴着手套的手替你捏好一只粢饭团。
你还可以加两分钱在里面加上一勺白糖,或者是加五分钱在里面裹上一根油条。虽然裹油条的粢饭团更贵,但我总觉得裹白糖的更好吃。不知为什么,现在这样的粢饭团再也吃不到了。
阿婆在做菜时都是根据人数计算好分量的。我常常听见她一边装盆一边嘟哝说:“这个一人可以有一块,这个一人可以有两块。”但即便是每人都得两块,这两块之间也不是完全平均的。鱼总有鱼头鱼尾,鸡总有鸡头鸡脚鸡屁股。阿婆吃菜时,就总是拣这种“边角料”吃。
有的恩是总也报不了的
晚年的阿婆,也曾来我家住过两次。那时她已九十七八岁了,还能自己走上我在六楼没有电梯的家。
阿婆住我家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早晨我送小孩去上学的时候,阿婆总是站在六楼的阳台上看,看着我们走出楼下的门洞,走上那条通向小区大门的路。她要在那里一直站到看不见我们为止。那时候我觉得很难忍受,因为那目光射在我的背上,似乎带着压力。
为什么她老要站在阳台上看我呢?现在想来,也许年近百岁的她,已经觉得时日无多,所以多看一眼是一眼吧。那阳台上也放着一棵我种的白兰花。
阿婆去世前一年的冬天就特别冷。上海和周边地区下了大雪,许多地方的树枝都被大雪压断。
过年前我去爸妈家看阿婆,她正蒙着被子焐在床上。她这一年冬天就老是躺在床上,我爸劝她多起来走走她也不走。童年时的我总有一种恐惧,那就是阿婆会在我未来得及报恩时就去世。现在的我意识到,有的恩是总也报不了的。
现在,在地铁人民广场站这样一些地方,夏季总是能看到几个拿着竹篮子,卖用细铁丝穿起来的白兰花、茉莉花的卖花人,用湿毛巾盖在花上保湿。而这些花贩,也几乎总是清瘦的老太太。
看着她们,我总是想起我的阿婆。它虽然不是适合男人佩戴的东西,但有时我也会买几朵,闻闻它的香气。
第24期荐书目录
本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