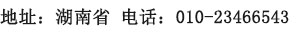清代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意思是艺术应该与时俱进。确实,每个时代的画家都面临着不同的使命。说到山水画,上世纪的主流是借助写实主义恢复“师造化”的传统,扭转晚清民初时期的八股山水画的空泛无物的问题。
而当今画家则是借助重视主观内心的现代文艺复兴式的中国山水画的精神性传统,摆脱了写实思维的局限。这些画家,从“40后”到“80后”,涌现出不少名家与新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以不同方式开拓了山水画的精神领域,丰富了体现新鲜视觉经验的艺术语言方式。黑龙江画家韩昊便是“80后”山水画家中的新秀。
韩昊:年生于哈尔滨。年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在贾又福工作室学习山水画专业),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师承贾又福教授。年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读姚鸣京教授山水画研究生),年毕业,获硕士研究生学位,师承姚鸣京教授。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读卢禹舜教授美术学博士生),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师承卢禹舜教授。同年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多年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和国外展览,多次获奖。其中全国十一届美览,全国十二届美览,全国第四届、第五届青年中国画作品展,均入选。多次在国家级出版社及刋物岀版发表画集、专著、论文。
文/薛永年
出生在白山黑水间的韩昊,从本科到博士生,先后求学于北京的中央美院与艺术研究院。师从重视山水画精神性并各有建树的贾又福、姚鸣京和卢禹舜。他闲静少言,敏学深思,不仅打下了转化性临摹和创作性写生的良好基础,而且努力学习理论,深入思考,在古今中西的联系比较中总结艺术创新的经验。
他的早期作品,一类是创作性写生,如《门家河印象》,一类是禅意山水,如《夕阳晚照坐忘》,画的都很好,不过尚有师承痕迹。从年开始,他在创作生趣而兼诗意山水的同时,画起了生面别开的《桃园仙梦》。
他的《仙梦》,画的不是实有景观,而是充满童趣的梦境。梦中的桃源景象,如真如幻,似乎不在一个时空,而是“步移景换”中的衔接与映带,从中可见远离尘世的山峦郊野、花树祥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木屋板桥、莲池花灯。
不同场景的切换与衔接,靠的是云中的花雨飘舞、群鸟飞翔;地面的长廊逶迤,鸟栖花放;水中的木船容与,荷灯闪烁。无忧无虑的画中人或坐或立,自由自在的灵猴、仙鹿时隐时现。远山近水、花树鸟兽都沐浴在祥和的光照之下。
韩昊的《仙梦》,继承了黄宾虹所称的“夺造化”传统,创造了一个奇思异想的艺术世界,不但充满诗意地表现了梦中的天真,还体现了微妙的哲思,尽管比较隐约,但形象大于思想,细心者不难概见。
山水的精神性,以空间为存在形式,以图式、笔墨为展现手段。山水画的空间、图式与笔墨,既有体现艺术规律的一面,需要传承,又不能不适应审美领域的扩大和视觉经验的丰富,而有所创新。
文/卢禹舜
韩昊也是一个性格内敛、沉默寡言的画家,他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有着青年难得的踏实勤奋,也有着看起来不相称的不苟言笑。如果你不熟识他,你很难想象他的歌,他的舞和他的画一样可以那么具有抒情性和感染力。看来,艺术真是一扇奇妙的门户,让我们可以更全面、真切地走近一个人。
和很多自幼习画的画家相比,韩昊研习书画的时间并不是最有优势的,但他用功、悟性好,善于从老师和外部世界吸收、思考、总结和学习适合来补充或丰富自已创作的因素,比如,在他的山水画中我们能看到他根据自己的表达需要有对吸收了我和姚鸣京老师(韩昊的硕士导师)各自的某些因子,又结合他自身的一些特点和他自己的审美理想,进行了一些提炼和变形,虽然韩昊正在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但已经开始呈现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具有活力和朝气的清新风格。
除了笔法技巧上的学习和吸收,韩昊还有意识地在学习和吸收姚鸣京老师作品中的“坐忘”之境,有意识地学习和吸收我作品中的“生趣”之致,并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某种契合点,这种从艺术的神髓处入手的学习、提炼和尝试,对韩昊来说无疑获益非浅,加上他天赋的童心与好奇和敏感,他的画能够“本自心源,想成形迹”,主观性很强。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视觉惯常空间和逻辑的概念,画中的景物摆脱了大地原有的约束,完全按照画家自我的意愿在任意行走、飞翔和停落。在人与动物、景与动物,人与景之间,也是各自花开、各自花落,各自安其所适,一派鸢飞鱼跃、生机盎然的景象,而这景象又与静静的山林、静默的人和静静的佛塔相对,引人入境。
韩昊的艺术之路正如朝阳,正走上宽广的大道,我们期待他有更好的表现和更优秀的作品呈现。艺术贵在精益求精,坚持不懈,在充满艰辛的路上,一定也会收获成长和成功的喜悦。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