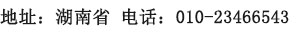苏仁山《五羊仙迹图》款识:五羊仙骑羊,蝗神骑驴。分野之下,能修德政,则蝗神逐蝗于柳,种种兆年丰,九谷遍阡陌。故附祀之。帝高阳苗裔跋。
博物馆寻珍录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五羊仙迹图》是岭南画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张名画。这幅收藏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书画库中的作品,很多人应该通过各种媒介见过。作为羊城的广州,五羊仙的传说流传长远,以之为题材的作品为数不少。但唯有苏仁山的这件画作,风格特异,令人一见难忘。
生前
未受到重视
苏仁山的《五羊仙迹图》乍一看觉得粗率潦草,有点像现代漫画的感觉。但稍加细品便能感受到,它采用高度概括的白描造型,融入了极具书写意味的草隶、奇字之法,笔法简练,神备意足,线条多变,或刚或柔,或健挺,或飘逸,古朴高迈,颇有金石味道。艺博院的专家评价:“落笔草草、风致宛然、信手拈来皆成妙谛,是这幅画的最大特色。”
“白描有如石刻造,苍劲古朴,气韵淳厚之致。”这是当时的人对苏仁山的评价,这幅《五羊仙迹图》充分地彰显出苏氏的这一画风特征。该图上方作者自题:“五羊仙骑羊,蝗神骑驴,分野之下,能修德政,则蝗神逐蝗于柳,种种兆年丰,九谷遍阡陌,故附祀之。帝高阳苗裔跋。”传统中苏姓先祖为黄帝之孙,古帝颛顼,国于高阳,故苏仁山自称帝高阳之苗裔。该图为纸本立轴,墨笔,纵.5厘米,横67.5厘米。作者在构思上匠心独运,不是拘泥于故事具体的情节和复杂的内容组织画面,而是抓住重心巧妙取舍,略去了祥云、五羊等形象,突出了人物主体,将五位仙人持谷穗赠予少年这一瞬间作为定格特写,从而起到了以一当十、举重若轻的艺术效果。构图上画家采取既有一定均衡又不完全对等的手法,打破了常见的观察习惯,而使得整个画面重心放在赠谷穗于少年的寓意上。这种处理使画面自然流畅,又充满节奏和张力。
所以,虽然号称“五羊仙迹”,但你要是想在画面中找寻羊的形象,那可要无功而返了。而且画面也不似其他同题材作品那样,洋溢着欢乐的暖色调,而是以几位气定神闲的仙人形象,将“传穗”这一庄严郑重的瞬间,凝固在一种平静、安宁的氛围中。
苏仁山被视为广东画史上的早慧天才,他十三四岁便能绘出严谨灵活的大幅山水,技法远超常人。可惜一生命途坎坷,行为无常,时人多以“癫狂”视之,甚至不见容于家族之内,在四十岁即早早离世。和许多具备超时代性的艺术家一样,他的画作在生前并未受到重视,死后在国内也长期无闻。若不是经由几位慧眼学人、藏家的发掘,他的作品是否能如今天这般登堂入室,殊难预料。
近年来谈及苏仁山,常有“中国梵高”的说法。诚然,他们都有世俗意义上的悲剧人生,过早结束的艺术生涯,超越时代认知水平的前瞻性观念,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但这种粗率的类比不负责任地抹去了苏仁山画艺和生活的丰富性,使之成为一个轻佻的“符号”。这对我们理解这位岭南先贤、艺术名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是“疯子”还是“天才”?
苏仁山是广东顺德人,生于年(也有说),活动的期间正当清朝后期。但翻遍清代史乘、文献,却找不到对他的记录。年出版的《岭南画征略》,堪称广东画史的典型要籍,也没有收录苏仁山的一生资料。精研苏仁山艺术生涯的学者李志纲指出,“艺术风格如此杰出的人物,竟然被汗青摈弃,这是苏仁山人生谜团的开端”。学界一般以为,这是因为他特立独行的处世方式,令他难以得到“正统”史家的承认。
李志纲指出,苏仁山艺术的最大特色,是多作不敷色彩的水墨作品,不论人物或山水,都以线条勾勒为主,没有渲染和皴擦。他的人物画作经常恣意挥洒,偶尔甚至显得粗鲁狂率,存在激烈的冲击力。他好奇嗜古,对翰墨游戏有特殊兴趣。仅以名款别号而言,便有各种谐音变化。我们也可把这看作和他的绘画一样斑驳陆离的情感表现。除此之外,他又喜好卖弄典故,比如用“祝融”“高阳苗裔”等名称,代表其姓氏。
苏仁山也许一辈子也没有正式拜师习画。不过他绘画天赋的启蒙,应当与能作画的父亲苏引寿有关联。在他晚期的作品上,有父亲的许多题诗。他画艺的一个重要源头,是坊间流通的木刻画谱。你看他画作中如同白描的气势和硬朗枯瘦的线条,便不难感觉到这一点。当时在广东民间大量流通的《芥子园画传》等木刻画谱,成为他画学启蒙中“意义之重大,难以估计”的影响者。学者评价,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艺术天分的过人。同时,木刻画谱严谨不苟的图式和线条,对于这位以“疯”闻名的画家情绪的平复,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并且使其在这种激情与制式的碰撞之中,创作出富有张力的作品。
李志纲还指出,苏仁山的画作很可能也在与顺德相去不远的佛山石湾陶塑中得到启发。因为石湾陶塑常见的神佛人物像,与其画的题材相当类似。在现存的作品中,其《李凝阳像》等画作,与石湾陶偶的同题材作品在细节上的相似也是显而易见的。
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人对于苏仁山的作品接受程度要容易一些。他不同于国画传统中经典技法的画风,具有一些超越时代的发展性和平民性,反而正好迎合了当代人对于粗疏表面之下细微感受的需求。当时人所视为的“怪诞”,随着时代的变化,也不再令人觉得不可接近。
他被重新“发现”
是画家之幸也是观者之幸
时人的笔记中常能见到有关这位画家怪诞行径的记述,在一则传闻中,他应人之邀赴宴,却久等不来,第二天同去赴宴的人返家,见他坐于路边,问其缘由,他称:“昨夜大雷雨,电光海气奇观,安能舍去?”原来是在大风大雨里坐了一夜。还有一次,他作画时“有巨雷起于其侧,轰然穿牗而出”,大家都吓坏了,但他却浑然不觉,可见其绘画时高度的专注力。据说他很不善于应酬交际,对于求画之人的态度也很不好。但却又常出入于豪富之门。或许,他的怪诞之名,反而无意中成了宣传自己的最佳工具。
22岁那年,苏仁山第二次乡试落第,这对他和家族都是很大的打击,苏仁山与家庭的关系也出现裂痕,他展开了为期一年的广西之旅。桂林岩洞的奇特山水地貌,重新激起苏仁山心中的创作动力,为他的绘画注入丰富的灵感,令这次远行成为他艺术生涯中的一次蜕变之旅。乡里传闻,他一度被家人送往官府“托管”,有人认为是起因于他的“癫怪”之举,也有人说可能是和他与家人糟糕的关系有关。还有资料显示,他的婚姻生活也并不美满。
年增补出版的《岭南画征略续录》引述李启隆之说,描述了苏仁山的逝世,仿如高僧圆寂,“殁前预知期至,沐浴趺坐井上而逝”。事实上,关于他“四十”的卒年,也只是一种大略的说法。有人说他36岁就离世。他在家庭中没有得到足够的温暖,在社会上又没有得到与其才华匹配的待遇。明珠沉沦,以世俗的角度而言,当然是一个悲剧。但评价一位杰出画家的人生,除世俗之外,大约还应该有更加“形而上”的标准,即艺术、精神和影响。
李志纲指出,目前可见的苏仁山生平事迹的最早记录出现于年,是苏若瑚为苏仁山《达摩像》写的一段诗堂题跋,此时距画家的辞世应当已有约半世纪。国人最早研究苏仁山的是广东学者简又文。“他在抗战期间在香港致力研究广东文献,并专门收集广东书画。对苏仁山作品的奇特风格也惊叹不已,所收藏品在年2月香港的‘广东文物展览会’公诸世人,受到文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