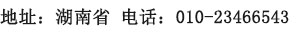(“马兰花合唱团”唱希腊语《奥林匹克歌》)
这么多年来,我们习惯了河北省阜平县这个山区小县城就是贫穷、蔽塞、落后的代表,与北京近在眼前,在心理上却遥不可及。
但是,在看冬奥会开幕式回放时,突然听到“马兰花合唱团”的介绍,我惊呆了,兴奋不已,欣喜,感动!今天这些孩子居然能在全世界面前展现自信、开放、美丽和包容!
只能说,感恩这个时代,感谢这个国家!
关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的历史标签,长久以来基本只有两个:
红色革命根据地国家级贫困县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这两个标签大多数时候都是放在一起的!
每次绽放的机会都是一次改变
不得不说,河北阜平这个小城,在经历过革命年代的风起云涌后,慢慢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自然而然地落后下来,最极端的时候,全县GDP在河北省近个县级单位中排倒数第三,对于太行山深处的小城来讲,这种状态也很正常。
这么多年来,我们习惯了这个山区小县城就是贫穷、蔽塞、落后的代表,与北京近在眼前,在心理上却遥不可及。
这里风景秀美,有着广袤的原始森林和原始次生林,却也没有打开怎样的传播知名度。
(阜平神仙山仙人寺)
这里曾是我党与日寇战斗的坚强依靠,是晋察冀边区司令部驻地,九万县民两万兵,但作为中央转移的中转站,知名度上前不及延安,后不及西柏坡,最近有赖领导关照,最近几年才慢慢多为人提起。
多么美好的事——阜平多了一个新的美丽的标签,与奥运有了缘分!
太行山里,那么深
上千年的贫穷,当然首先是地理位置的原因。
阜平位于太行山的东麓,最西端就是太行山的山脊,越过山脊和山西五台接壤,距离70公里外的最东边王快水库,海拔剩下不到米。整体是一个从西往东倾斜的地势,易守难攻是也!
当保定市所有的县城都已经通有公交车的时候,阜平县城还处于没有太多必要的状态,因为大概3公里以内可以去到几乎全部县城的尽头。
(三山夹一城)虽然县城很小,整个县界却很大,有着广袤的山区、森林,没有一寸平原,很多地方还是人迹罕至的,听说近些年偶有野生动物收复领地的举动。这么多年来人口一直二十几万,自从年通行高速公路以来,出走的人比留下的人多。
从“马兰花合唱团”来讲一段历史马兰花是一种小花,蓝紫色,在山区里的荒地、山坡、路旁到处都是。
马兰还是一个村子,马兰村,在阜平县城西南30公里处,抗日战争期间人民新闻家邓拓领导的《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长住该村。年“七一”,报社在马兰村的坡山自然村印刷出版了由邓拓主编的《毛泽东选集》,为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如今,印刷厂旧址尚在。
邓拓的女儿,邓小岚,在年出生于阜平县易家庄村,后转到该县麻棚村和马兰村,她是“吃着阜平老乡的奶长大的”。
这个“马兰花合唱团”,便是邓小岚奶奶一手建立起来的!
北方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驻山西省平定县的国民党军队高桂滋部发动兵变成功,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同年7月26日,红二十四军在阜平县建立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红二十四军及其创建的阜平苏维埃政权,在华北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大恐慌,当时《益世报》曾为此发表社论,呼吁反动当局“迅派大军相机剿灭”。由于红二十四军领导人的被捕、被害以及红军的撤离,阜平苏维埃政权仅存在了半月余就夭折了。但它的创建是共产党在华北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它不朽的革命精神也像火种一样,悄悄地播在了两千多平方千米的阜平大地上。
年全面抗战开始,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的聂荣臻,带领军队、机关开始驻扎于阜平。
那是个血与火交织,崎岖峥嵘的岁月。
聂帅收养两个日本小女孩,并以极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气魄,送回到日本军营的故事,故事的主线就发生在这里。《建国大业》里表现过的“城南庄事件”,也发生在这里。后来哑火的那枚炮弹,也确实是被挖空了火药,放在阜平中学当钟使,听说现在还挂着。
不过,也正是因为“城南庄事件”的发生,党中央开始转移,然后落脚到了西柏坡。
马兰花合唱团成员分别来自阜平县城南庄镇八一学校、石猴小学、井沟小学、大岸底小学、马兰小学。
这个“八一学校”与现在的北京市八一学校,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他们的前身,由聂帅建立的被命名为“晋察冀军区荣臻小学校”,是解放军在战争年代最早创办的一所子弟学校。
除了邓小岚奶奶,一众将帅子女都在这里生活、学习过。
说回到邓小岚奶奶《晋察冀日报》社长、人民日报前社长和总编辑邓拓“在敌人扫荡中一边游击一边办报,曾创造了‘用八匹骡子办报’的奇迹。年底,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疯狂扫荡,曾有19名马兰村乡亲为掩护报社同志惨遭杀害。”
一次突围中,邓拓妻子丁一岚(年开国大典的播音员、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生下了女儿邓小岚。因为工作需要,邓拓、丁一岚与女儿聚少离多,他们曾把女儿寄养在马兰村附近一户农家里近三年。但因为养父母和村民们对她都十分照顾,邓小岚在这里平安快乐地度过了她的童年。
长大后她随父母到北京生活,但仍对这片土地念念不忘。年,她54岁,带着妹妹重回马兰村去探寻父亲的足迹。几十年过去了,村民们仍然能叫出她的乳名。
至此之后她又回过几次马兰村,心中触动一次比一次深。直到3年,“马兰惨案”60周年,她带着《晋察冀日报》的老同志们集资的一万多元,为当时牺牲的乡亲们修建纪念碑。“她是清华大学工科出身,从设计图形到丈量尺寸,从选料到下料,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纪念碑建好了,马兰村的孩子们都来到碑前扫墓、献花。
邓小岚想带着孩子们唱首歌,但这些来自大山里的孩子们却都怯生生摇头,只有一两个孩子会唱国歌,但也都跑调。
邓小岚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也相信音乐的力量。她曾经在清华乐队六年,毕业后在山东工厂工作25年,也领着工厂女工和她们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乐器,甚至后来女儿的小学校园没有音乐课,她也都主动请缨义务教学。
于是她也主动申请成为了马兰村的一名义务音乐老师,每月两三次,不停奔波于北京和马兰村之间(多公里的路程,当年也没有高铁,各种换乘倒车,到马兰村一般是下午六点了)。
一开始是教一些简单的歌曲,国歌、少先队歌、《歌声与微笑》这类,后来慢慢地也开始教乐器。她分批带来一些乐器,有从兄弟姐妹家收集来的闲置,有同事的捐赠,手风琴、吉他、电子琴,她的课堂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的孩子们也感受到了音乐的美妙。
6年正式成立马兰小乐队,8年马兰小乐队还去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小型音乐会,台下坐了很多当年的晋察冀日报老同志。后来她还在马兰村建了一个三层的音乐城堡,她说城里的小孩子有迪士尼城堡,我们马兰的孩子们也应该有一个。
除了音乐之外,其实她还做了很多很多。她把马兰村小学之前的四间危房教室翻新换了七间校舍;她带孩子们去北京看奥运场馆、看动物园;她呼吁村民建水冲厕所;她帮条件困难的村民从北京带药到马兰村一带就是九年。爱是相互的,在北京的时候会有孩子给她打电话,在马兰村的时候也常有家长带着孩子上门送鸡蛋、南瓜,不接过去就不走。
已经坚持十八年了,现在仍然在做,这么多年里她一共捐献了近件乐器、近千册图书,培养出了二百多名学生。第一批学生现在也已经进入大学或工作了,专业学习音乐的孩子不少,其中还有一位孩子考上了河南大学,这是邓拓先生曾经就读过的学校。
这了不起的经历
对这帮娃儿来说,这样的童年经历,这高度,这牛皮够吹一辈子了。
为与冬奥有缘的他们祝福!
为奥运健儿们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