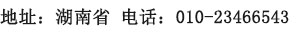《禅观画事》连载六十九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中国画艺术“畅神”说,是指精神的物我通达,气息的天人流畅。不但是画者作画进入了“神之所畅”之境,亦是观者闲对画作时生发出“畅神”之幽思与愉悦。无论画者还是观者,所能获得的“神之所畅”之幽思与愉悦,与参禅者在平时禅道修持中的空静观照思维蓄养间之惮悦感应是相通的。
“卧游”观,一方面显示出他陶醉于自然山水之情怀;更有深远意义的是,拓展出欣赏山水自然一个广阔的艺术心理空间,并将山水画艺术的品赏思维提升到一个出神入化的神游境界。当进入年老体弱的人生阶段,不能到苍山野水之中游历了,把游过的名山大川画出来,张挂于壁,有的还直接画在白粉墙上。时常靠在茶榻上吃茶、品酒、弹琴,并观赏画作,这就是他所言及的“卧游”,达成他“面对山水,澄怀观道”的心愿,满足他“万趣融其神思。
王孟义写意山水作品
宗炳的卧游观与畅神说
前面已经谈到的南朝·宋时期的宗炳,精通老庄、易学、佛学,也是热衷于谈玄论道的名士。他在其著《画山水序》中提出的“山水以形媚道”正是发端于当时炽盛的玄思。他主张的山水画“画象布色,构兹云岭”的营构要旨是:“理绝于中古之上,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这些都属于玄思范畴。他在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基点上,进而提出“澄怀观道”的思想,指出“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的审美思维途径。在宗炳的审美思想中,认为悟得自然之道,不但是人生的最高追求,亦是山水画艺术的最高追求。他将“栖形感类,理入形迹”的物我交融观,作为画者挥毫“妙写”之至要法门。他认为画山水之形,更重要的是将天地自然之道,万类物象所隐现的“理”,融入所画的万类形迹之中,这才是一个画者对天地自然的虔心尊崇,对万类物象的真诚倾诉。这其中阐明了对“山水以形媚道”之真切体悟。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思想,无论表征目标是任何物象,必定会与天地自然相联系起来,终归的指向都会是道。对天地之道的体悟,对万物之理的思索,必然是在“言象之外”所进行的思维探求之玄思妙悟,这正是中国画艺术与禅相遇之处。“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画道必在妙悟!画者惟妙悟生发妙想妙念,笔底方能达成宗炳所说的“妙写”之艺术境界。
王孟义写意山水作品
宗炳在《画山水序》的最末一小段中说道:“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聚,独应无人之野。峰岫绕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这即是观者闲对山水画作品欣赏的一种幽思描述,亦正是观赏者的一种神游情状。紧接着的是文章的结束语:“余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熟有先焉?”宗炳于此特别强调了山水画艺术的审美功能只在“畅神而已”,肯定了画作中“神”的内蕴之重要,“神之所畅,熟有先焉?”此处的畅神,是指精神的物我通达,气息的天人流畅。不但是画者作画进入了“神之所畅”之境,亦是观者闲对画作时生发出“畅神”之幽思与愉悦。无论画者还是观者,所能获得的“神之所畅”之幽思与愉悦,与参禅者在平时禅道修持中的空静观照思维蓄养间之惮悦感应是相通的。古今诸多高僧大德以禅入画,其实大多都是在画作中抒发此类禅悦感应。平时赏读禅画,亦须观赏者略具一点禅心,方能由画作神韵的牵引生发禅思,领悟到禅在画作中的意蕴,观赏者由此获得的愉悦感,既是一种“畅神”感,也是一种“禅悦”感。
王孟义写意山水作品
《宋书·宗炳传》记载:“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由此可见宗炳平时钟情于自然山山水水的心志。宗炳在此提出了“卧游”之说,一方面显示出他陶醉于自然山水之情怀;更有深远意义的是,他拓展出欣赏山水自然一个广阔的艺术心理空间,并将山水画艺术的品赏思维提升到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他进入年老体弱的人生阶段,不能到苍山野水之中游历了,把游过的名山大川画出来,张挂于壁,有的还直接画在白粉墙上。时常靠在茶榻上吃茶、品酒、弹琴,并观赏画作,这就是他所言及的“卧游”,达成他“面对山水,澄怀观道”的心愿,满足他“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的目的,这正是中国画艺术的神游观的一种方式。以禅心观照思维而言,卧游、畅神,都是禅的“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纯精神性心理愉悦,即是地地道道的禅悦。(《禅观画事》连载六十九)
王孟义写意山水作品
王孟义写意山水作品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